


也曾作念过农民、代课老师的牛二哥迫于生涯成为货车司机。他所在的车队曾行驶数沉之远,到达荒无东谈主烟的人命禁区,在那儿,货车司机们面对着难以联想的危境,也见到了无比颤动的好意思景。在新近出书的《货车司机牛二哥》这部非臆造作品中,牛二哥与一同开货车的一又友们,以小个体的视角见证了大期间的变迁。
节选
1
2003年7月9日上昼,咱们在格尔木市南郊列队洗车。因为钾盐能腐蚀汽车的扫数部件,频频拉盐的车子,车架、电路、橡胶件等的使用寿命比一般的货车短得多。
趁着列队的破绽,我溜到外面给家里打电话报祯祥。我的三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算作援藏干部在藏北责任过好几年,和我父亲聊过那儿的环境,因此给父母打电话时,怕他们记念,我没敢说实情,啥好说啥。浑家的电话打欠亨,我心里很心焦。想再打时,车队又要开动了。
回到车上,黄毛肃静苦闷,两眼泪汪汪,瘦小的身子瑟缩在卧铺上。家庭的繁难,女一又友的不睬解,压得他喘不外气来。一把刀气定神闲地坐在副驾驶座上,为了打刊行将到来的缺氧,早仍是扔掉塞在鼻孔里的纸团,手里拿着金黄色的蜜橘,一边剥一边玩赏窗外稍纵则逝的景观。其实,他的内心并不坦然。
安多海拔四千八百米,讲理干燥清凉,空气疏远,是一个凄沧的全国。除非村生泊长的藏族东谈主,外地东谈主很难合适。据说铁路局的工东谈主在藏北施工,三个月要回格尔木轮休一次,一次休息一个月,即是为了驻防内脏器官发生变化。我的指甲从藏北纪念以后出现凹下,两年后才复原平素。
司机们齐说安多一天有四季,六月飘大雪。拍拍我方的小身板,嘱咐顶不住高原隆冬?想想我方那鱼鳔似的肺,接纳氧气的速率行不成?想前想后一阵子,尽然缺氧似的喘不外气来了。

过了南山口检查站,车队拉开了距离。青藏公路格拉段路面极好,全是刚铺的柏油路,双向两车谈,稍窄,每一个拐弯处齐有路标。据说这条线最早是军管的,运行不信,自后看见养护公路的是武警,才知谈此言不虚啊!
两个小时后,来到了不老泉。在青藏公路左侧,有一座凉亭,亭前立着一块石碑,上头写着“昆仑神泉”。来到亭内,一泓清泉汩汩而出,像鼎沸的滚水,又似一盘碧莲。据说此为王母圣水,能治百病,大伙儿忙着拿多样器用灌水。饮之冰凉,但很好喝,甘甜润喉。
老黄站在亭旁,仰望巍峨兀立的昆仑山,鸟瞰碧水潺潺的清泉,顿感心潮澎湃,诗兴大发,口占一首《昆仑神泉》:
昆仑山中一亭台,
碧波晃动欲漫沿。
手掬一捧甘如蜜,
众客疑为天上来。
大伙儿听完,纷纷为他饱读掌叫好!
参预可可西里保护区后,碧绿的草地,周折的小河,朵朵白云九牛二虎之力,巍峨昆仑繁密壮不雅,芜俚来到了鱼米之乡!小鸟在解放颂赞,藏羚羊在成群地驰驱,石羊在得志地吃草,还有那顽劣的旱獭,扭着臃肿的身躯,在痴痴地看着战争的车辆。
特地根由根由的是,因为海拔高,莫得树木,这里的小鸟就在草地上洞居,它们尽然抢占了小鼠兔的家。看着小鸟从这个洞口进,从阿谁洞口出,蛮根由根由的!路两侧有挑升的动物通谈,供多样动物安全通行。
过了索南达杰记念碑十几公里,有两个东谈主站在路边拦车。司机们纷纷下车,有“放水”的,有行径形体的。孟老大和孟老二还强颜欢笑,面对面地切磋了一下太极推手。中站的杨得胜一下车就朝轮胎上撒尿,三蛋看见了就见笑他:“得胜,注意轮胎炸了,把你那东西给炸飞!”
杨得胜把握甩了甩,说:“齐说东谈主过四十三,裤裆常不干,老子还不到三十四,咋就忽闪其词哩?”
老冯说:“没事儿老弟,到了安多给你挖些藏参补补,保证让你迎来第二春。”
2
此时,只见老黄、二驴和一个生分东谈主一边言语一边向我走来。
蓝本是中铁十局的一辆越野车推论“勘测”任务时,在距离国谈几公里的所在被困住了。两个司机来到路边拦车求救,赶巧看到咱们的车门上有“中铁十九局”的标记,于是拦住让帮个忙拖车。
为稳健起见,老黄让我开车去。我天然有点不宁肯,但如故得征服涵养。
其他东谈主接续起程,按商定晚上在五谈梁会合。

我开着货车随着老黄的皮卡驶离了109国谈,参预一条便谈。路面崎岖起义,颠得把握的一把刀直吐酸水,嘴里嘟哝着,挟恨老黄吃柿子专挑软的合手。四相当钟后,咱们才到达陷车的所在。
下车后,咱们来到车子前边。阿谁小车司机真的个仙葩,放着好好的正途不走,不知何如尽然一头扎进了把握的一个沙坑里。
阿谁小伙子惊魂不决,指着车子对老黄说,赶快意见弄出来吧,这个沙坑是活的,车子还少许少许往内部陷呢,当今的位置比刚才下沉得更深了。
可可西里的流沙是挺恐怖的,在马海拉盐时我就听青海的司机说过。流沙底下其实是池沼,可可西里是高凉讲理,冬季隆冬时有的池沼被冻住,春季风沙大,严重沙化后名义的草没了,只剩下沙子表露在外面,变成大地鉴定平坦的假象。到了七八月份池沼运行消冻,汽车轧上去俄顷就会被吞没,这即是可可西里东谈主车失散事件多发的原因。
这两个司机的命运还算可以。当今是7月份,刚刚运行消冻,可可西里最关怀的时候是8月份,要是发生在其时,这二东谈主料到齐投进大地母亲的怀抱了!
钢丝绳挂好以后又面对一个问题,铁路局阿谁年青司机说他腿软发怵,生死齐不肯意再上车了。然则陷得那么深,必须两个车合营着材干拖出来。我心里有点不满:发怵,谁不发怵?谁也不是九条命!生死关头装屎,是不是男人汉?
老黄看了看我,知谈不成,牵引车必须老司机开;他把眼神移向二驴,二驴吓得头摇得芜俚拨浪饱读,说:“黄哥,饶了我吧,我当今仍是快尿裤子了。”
“鸭子毛,没用的东西!”老黄骂了一句。
老黄又将眼神瞄准一把刀,此时的一把刀后悔得死的心齐有了,怪只怪我方此行搭错了车,赶忙摆手谈:“黄……黄队,我……我只会抡勺子,不……不会开车!”
老黄说:“鸭子毛,一把刀,在盐湖的时候,为了过把瘾,你开着三蛋的一号车齐快飞起来了,还说不会开?”
一把刀尴尬一笑,那豪情比哭还丢脸:“黄……黄队,我上有老,下有小,你……你……”
老黄无奈地叹了连气儿,终末将眼神投向了孱羸的黄毛。

黄毛哀伤地环顾一周,铁路局的两个东谈主脸扭向了一边。他的眼神又从老黄、二驴、一把刀的脸上逐个扫过,几个东谈主色彩各别,有压迫,有怂恿,有崇尚。他转过身,看了我一眼,说:“牛哥,你多用点劲,咱按喇叭为号。”然后迈开沉重的步子,肃静走向被困的车子。
看着他下到坑里,掀开车门,钻了进去,车子一颤,又陷进少许,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“走、走、走!”老黄摆手涵养着。我逐步加油,钢丝绳迟缓绷直后,按了一下喇叭,车子轰鸣着运行加力。轮胎刨着大地,沙砾打到车门上“叮当”作响,小车少许少许被拖离沙坑,眼看着就要出来了,顿然,钢丝绳“砰”的一声尽然断裂了。
“啊”的一声惨叫,半截钢丝绳画了一条曲线,尾梢扫到二驴的脸,那张黑脸上平添了几谈血痕。
失去拖拽的越野车向下一栽,俄顷又下沉了好多。老黄急得高唱:“二驴,还有钢丝绳莫得?”
此时的二驴顾不得脸疼,像山公相似,马上爬进车厢里,“嗖”的一下,又扔出一条比刚才那条粗得多的钢丝绳。
老黄见了,气得骂谈:“鸭子毛,二驴,刚才为啥不先拿粗的,且归看我何如打理你!”
一把刀和中铁十局的司机顾不上听他埋怨,赶紧挂钢丝绳。一把刀边挂边喊:“别说了,黄队,再不合手紧,黄毛就要完蛋了!”
很快,又一声喇叭响起,那辆泥孩子相似的车子终于被拖了出来。
3
晚上十点到了五谈梁,才知谈车队在这儿莫得加上油,仍是去了二谈沟。老黄让咱们先在这里休息整夜,翌日早起再去二谈沟会合,他们开着皮卡先走了。
吃力了一下昼,咱们三个东谈主又累又饿,看见路边有一家好又来川味饭店,门面不大,墙上写着“河南山东,河北辽宁”几个大字,俄顷有种回家的嗅觉。掀开厚厚的布帘,繁荣兴旺的暖流就扑面而来,屋里屋外几乎是两重天啊!房子中央有一个火炉,炭块发出蓝色的火焰,一把大肚小嘴的茶壶放在上头,水开了,冒着一缕缕的蒸汽。坐下以后才嗅觉到脑袋有点沉沉的,似乎被灌进了些水银,轻轻一晃就吞吐作痛。我问了问他们两个,齐有点调换的嗅觉。此地海拔四千四百米,何况屋里生着炉子,含氧量天然少,料到是有点高原反馈了。
雇主娘是个漂亮的四川女东谈主,她一面给咱们倒水,一面说:“‘到了五谈梁,哭爹又喊娘’,有点反馈是平素的,我看你们几个壮爷们儿应该没事儿!”
一把刀从口袋里掏出烟和打火机,“啪啪啪”摁着即是打不着火。雇主娘从柜台里摸出个打火机扔给他:“来到这儿,平庸打火机、洋火齐不成,缺氧,啥齐得用高原型的。”
菜是黄毛点的,新疆大盘鸡,嗅觉还没多弥远间就端上来了,满满的一盘子,色香味俱佳,还挺实惠。几个东谈主像是三天没吃过饭,狼吞虎咽的,没一会儿就祛除干净了,终末又下了几单方面。雇主娘坐在一边,看着咱们的吃相一直在笑。
一把刀算作专科东谈主士,运行吃的时候还品头题足,指点着几处不及,什么齐说了,即是莫得说面片有点不熟。
整夜无事。第二天凌晨,我就感到肚子不欢悦,接连上了几次茅厕,我方也莫得贯注,平时跑车饥一顿饱一顿,胃不是太好,向雇主娘要了几片药就启程了。然则,一谈上如故不断地腹泻,东谈主很快就没了精神,无奈只可让黄毛开车,我躺在卧铺上休息。

到了二谈沟加过油,一把刀转了一圈也莫得买到药。咱们一直到了沱沱河,才看见路边有一家铁路病院。一把刀陪着我去找东谈主看病。一位一稔白大褂的中年女医师给我检查了一下,说是急性肠胃炎,但是很缺憾无法提供支援。问其原因,医师说这里的工程行将戒指,病院莫得药,打针盐水也落伍了,提倡我立即复返格尔木。
她说的话咱们难辨真伪,一个正规病院尽然连平庸的药品齐莫得吗?一把刀恨恨地说,把我方的腿打折他齐不会投降。唉,咱们这些大货车司机长年在外,际遇的冷言冷语多了,对被东谈主欺凌、遭东谈主绑架的事儿也风尚了。多一事不如省一事,东谈主家医师不想管你也平素,然则想想我方昨天还救助过别东谈主的事儿,心里就以为不是味谈。
黄毛在一个小药店买了些药,料到是假的,吃了以后少许齐不起作用。
乘车复返格尔木去,这个念头我想齐莫得想过,平时我方形体好得很,嗅觉挺一挺就能往日。路上又拉了几次肚子,脱水严重了,手背上的皮一下子能揪起很高,下车肤浅时亦然出溜着下去,上车时得一把刀拽着才行。
下昼4点,到达三江源,这里是母亲河长江、黄河的源泉。旅游的东谈主好多,但是环境轻侮也很严重。我在河南老乡的一辆半挂车上要了两板药片,吃了以后,徐徐睡去,到了雁石坪后才醒来,此时药片起了作用,东谈主嗅觉欢悦多了。
翻越唐古拉山时,又下起了漫天大雪,我强撑着再次接过标的盘,注意翼翼地行驶。来到山顶时,一辆半挂车翻到了路沟底下,我和一把刀冒着风雪找到了司机,他们搭上咱们的车子去了安多。
与车队在安多县城会合时仍是是晚上11点钟。草草吃了饭,我又驾车跑了整整整夜才到达错那湖工地。
至此,青海之行告一段落,我在藏北生活的序幕行将拉开。本文虽以“青藏”算作起头,其实给我留住最深印象的如故在安多的半年生活。在这里,我的躯壳与精神际遇了此生从未履历过的残害,其间履历过“捞鱼风云”“压沙区打仗”“藏族东谈主扎西”“午夜淹没的女东谈主”“微妙蒙古包”等事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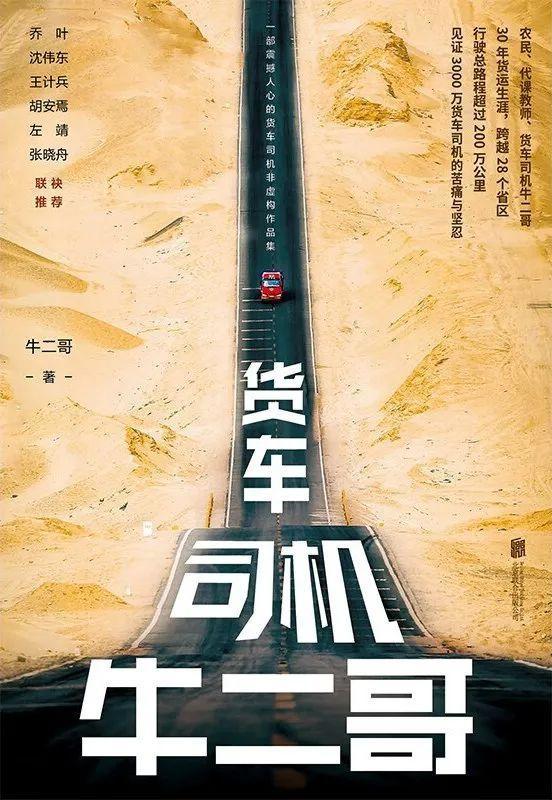
选自
《货车司机牛二哥》
牛二哥/著
玉兔文化·北京蚁集出书公司2024年11月版
新媒体裁剪:张滢莹欧洲杯下单平台